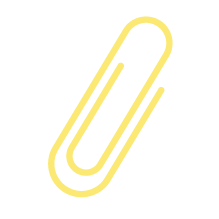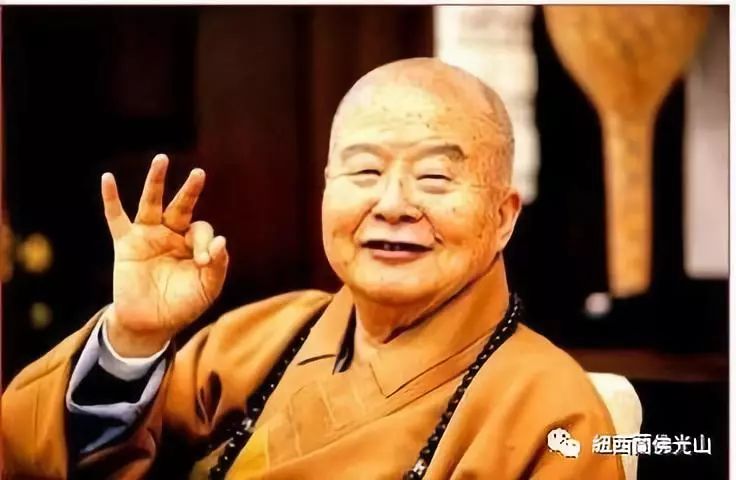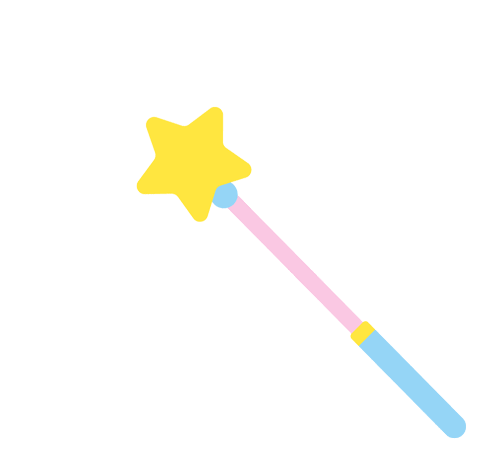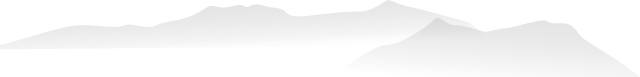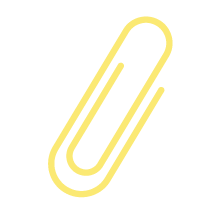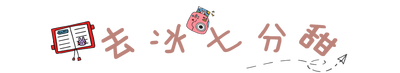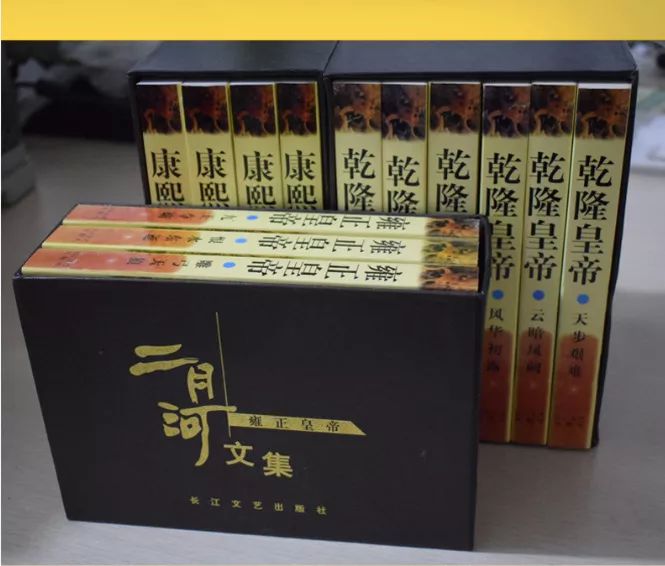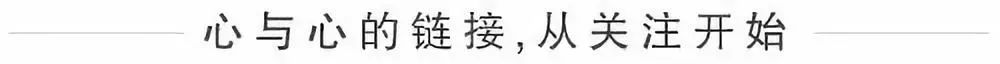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继《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后另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以下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的编者对这部重要著作的说明: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述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见本卷第470—471页)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见本卷第479页)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565页)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见本卷第564页)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页)马克思还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570页),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573页)。
这部著作是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就动笔撰写的,马克思把它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显然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改行帝制。1851年12月2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称这次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7页)。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最初计划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 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他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定了原文,把书名更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批判了维·雨果和皮·约·蒲鲁东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的唯心史观,强调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指出他的这部著作旨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见本卷第466页)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恩格斯对第二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并为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见本卷第469页)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同年1月7日—11月12日分32节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这一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版,1894年出版了俄文版。
收入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版译出的,并收入了恩格斯为1885年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对1852年版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