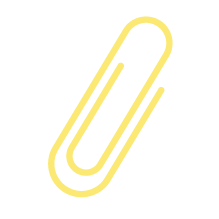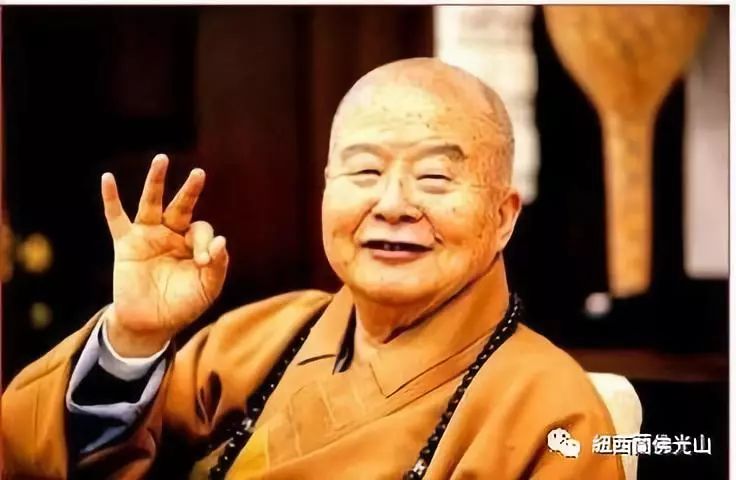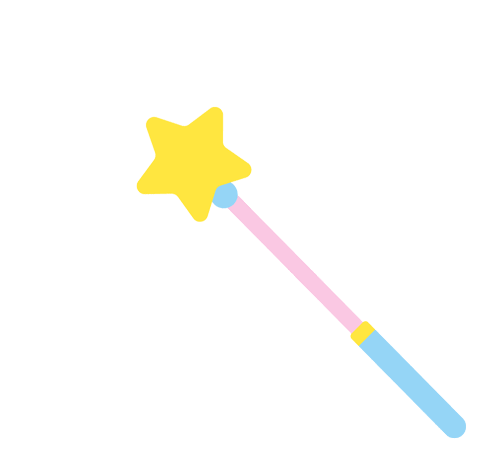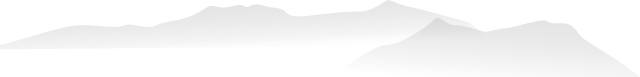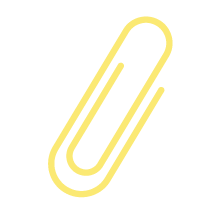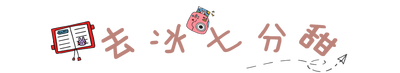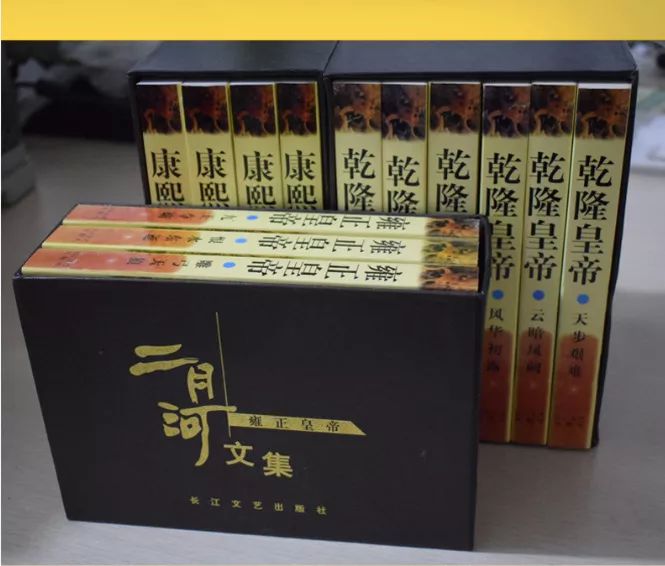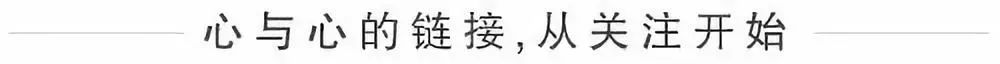致更年轻的一届
作者介绍
程伊泽
2018届分校文科30班毕业生
外语类保送
进入复旦大学法文系就读
现在这个时候,上海一间小屋子的桌前,我把台灯和屏幕调暗,摘下耳机,心里有很多涌动着却未成形的想法。去年此时的郑州,再过五六天就该供暖气了;我们每个早晨再也不用害怕迟到,慢悠悠地吃完饭才把手紧紧地揣在兜里,一边喷着白气说着话,一边向旁边国际部楼里的实验室走过去。推开门,屋子里有的眼睛会抬起来向这边打探,有的还是随着读书声一致地在纸上流动,最开始的日子里这些眼神都有些冷淡,但渐渐地它们变得亲切温暖起来。我会在天还没亮透之前去后面的饮水机里接热水,看着它滴在红褐色的茶包上,然后释放出稍浅一点的红褐色。从七点到七点四十左右,是大家沿袭下来的早读时间。人们参差不齐的站着,要么是一时兴起,要么就是习惯使然。这是一天中最嘈杂的时候,尽管大多数人都在念英文,但内容还是颇为不同;我的那本专八词汇,在身旁新东方美文或是某某名人的演讲稿之下也显得多少有些安静。从早读到第二节下课,这是我背单词的时段,尽管当然会困,也会无聊。每天一个单元的工作量,说实话并不轻松,但早晨毕竟是我规划中认真学习的时间啊。
但下午就不尽相同了。可能多数时候会接着上午的内容再多写几节课的题,但斜射过来的阳光总会让人心情舒畅,而心情舒畅的我便会找其他人一起下楼去打球。过往两年多被国际部压榨的球场似乎一夕之间唾手可得,这样的满足感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和清华周学长打球时,刚刚扬起手要投篮的时候却远远瞟到再熟悉——其实说是畏惧更恰当——不过的、班主任贺老师的身影。“完蛋!”然后扔下球就窜进了教学楼,那样的场景称之为狼狈简直不能再合适。当然我和周学长还有其他的一些事迹,但这里写出来也多少有些不正经了。
我对于晚上的记忆就是,身旁的光如何逐渐在冷暖明暗之间变化。阅览室和实验室里,最熟悉的吊灯不会给屋子留下什么阴影,冷淡得一视同仁;走廊里会是暗黄色的壁灯,随着我的步伐带我从亮走向暗,又逐渐走出来;或许我们会进到一个教室里练习面试,这样的话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就在许多的英语和不时泛滥的汉语中度过,当然还有一直没有彻底消停的笑声;或许踏出走廊就标志着这一天学习生活的结束,接着就是看着影子由长变短,由前至后,在白色与黄色的路灯之下交替,最终周而复始般地回到寝室的吊灯下。
而所有这些日子夸张些讲,我都是戴着耳机度过的。当时的我可能开始嫌弃酷玩后期的电音和杂乱,可能尝试着思考迪伦与科恩的歌词,可能沉浸在几只伦敦或是莱斯特乐团的另类摇滚中。彼时的Apple Music对我来说简直是最初和最后的天堂了,数不清的essentials歌单给了我对于许多传奇艺人的第一印象。而圣诞节时各色各样的圣诞特辑是我感受到的唯一节日氛围,而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到雪花、红灯泡以及圣诞树,以及所有给人些许幸福感的事情。
从十一月到一月,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那么现在,复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当然了,这是一所被贴上许多标签的学校;每个人都看到各种平台上写的“自由而无用”(我拒绝后面那三个字,听起来实在有些out fashioned),而你们或许会像我当时一样,感受到些许心潮吧?我记得暑假里有一次坐车回家,一路上都在看“在复旦大学就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复旦大学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气质?”,这种东西。但其实这里不会有人把所谓自由无用挂在嘴边,尽管他们还是会认同这个说法。在这里我尝试着发出第一个小舌音,写下第一个开音符,记下第一组动词变位……这是一串能写到天亮的句子。每个星期楼道里和公众号上都会贴满讲座与沙龙的预告,而往往有些很是吸引人:巴黎高师某位老教授讲波德莱尔的主体性,王安忆谈改革开放几十年间的变迁,不时还会有某位诺奖得主来讲些我听不懂的题目。而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会坐在光华楼前的草坪上,讨论、交流、看书、吃东西,当然还有谈恋爱;会在九点钟走进三教,买杯咖啡,开启不眠的一夜;也会经由政通路的水杉与灯光去往五角场,从校园去往商圈。而毕竟复旦没有宵禁这种说法,就算夜里三点也会有人刚刚从灯光下走出,独行或牵着手,走向一场迟到的睡眠。
而如果你们会像我一样幸运,有许多朋友在江浙沪的话,到时候就凑个假期好好聚一聚吧。带他们去安康,那家复旦人的酒吧,就着店内的北方气息吃些烧烤;一起打游戏到两三点,然后从学校骑自行车到外滩,看太阳从那些高楼中间升起来。清晨的风很凉,就是那种很适合喝胡辣汤的天气。于是又骑了很久找到一家写着“河南胡辣汤”,藏在一个菜市场里面的小店,虽然味道不很好,但也算了却心血来潮。这便是我在这里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写到现在我当然也觉得这些内容没什么帮助,但我又该怎么来传授所谓经验呢?所有的经验都被人翻来覆去地讲过,而不出意外的话你们也翻来覆去地看过了。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建议,我会建议各位多读些书,多看些电影,多听几张专辑。因为我最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想了解的太多而自己真正了解的实在太少。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我在向你们传授经验,但在每一所学校的课堂上、教室里、图书馆中,我们都只是智识的低地,等待着溪水向自己奔流。无论是文字、电影还是音乐,乃至夜里的灯火,路上的行人,刚刚更新的游戏资料片,伦敦进行的一场球赛,女生脸红着接受的表白,没有什么知识应当被冠以无用的名号。
话虽如此,我还是希望各位能明白,知识的获取应当是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别的。法语专业的学生——像我——就自然会以法语作为学习的重心;而身处高中的学生——像你们——最好还是把每一门课业都当作现阶段的任务。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乃至抱怨体制,起码在萨特看来,外在环境不该成为人的借口,每个人的模样正是由他自己的选择所构建的。
欢迎关注
郑外校友会官方平台
「郑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