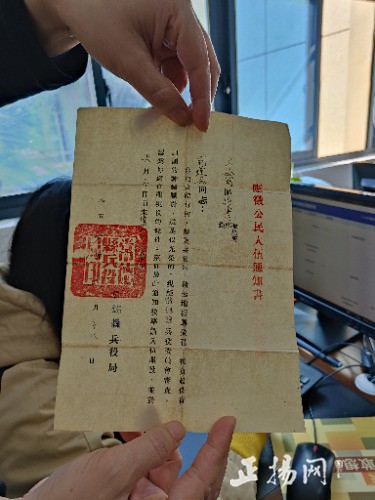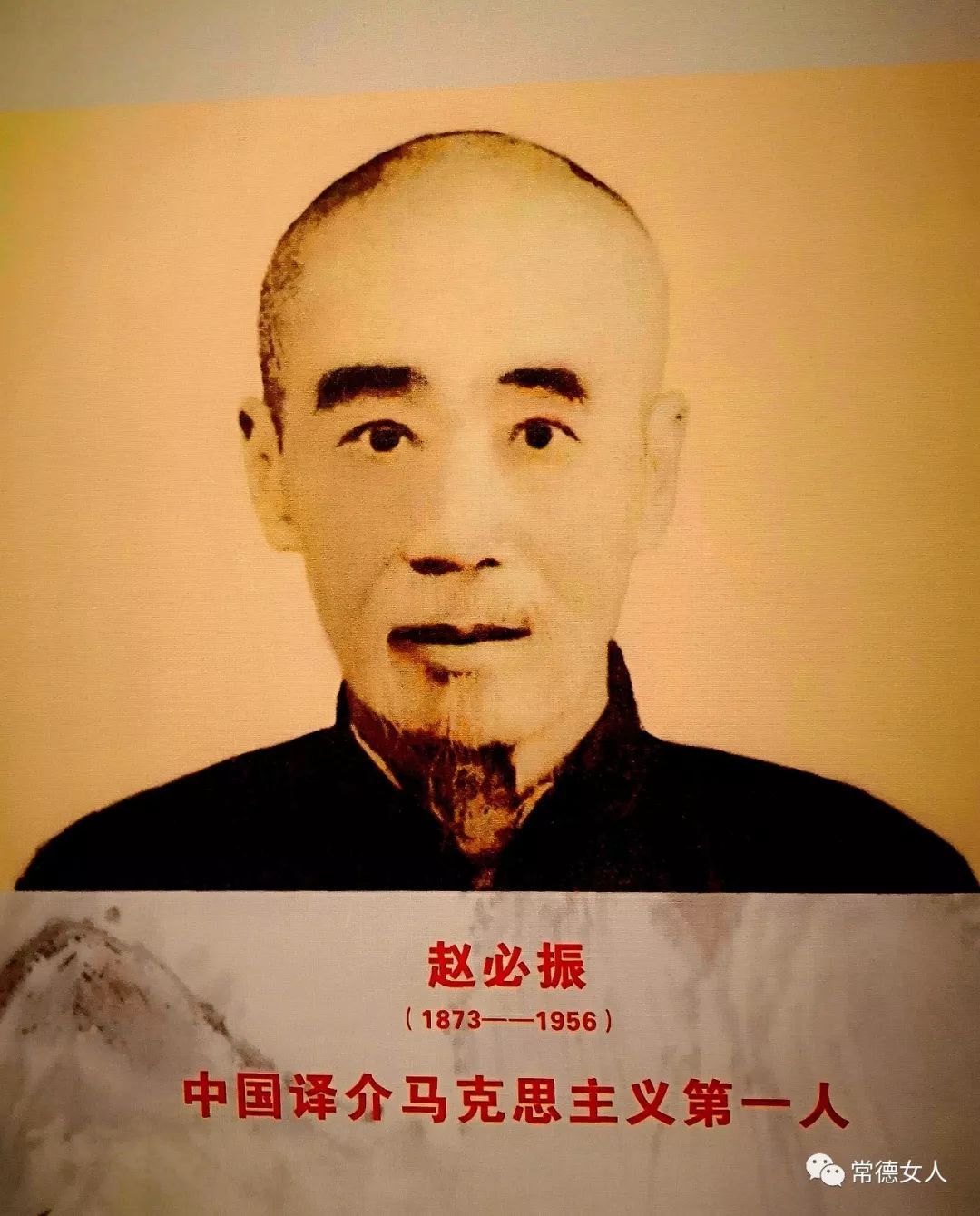文/覃旺成
在六七十年代,记忆中的稻草垛,硕大、硕大的,象一团又一团的金黄色的蘑菇云,袅袅婷婷地升腾在农村的天地间。当快到晚饭时分,农村家家户户的屋面上,象比赛似的,冒出一缕又一缕的炊烟,氤氲一般,吞噬着稻草垛。炊烟和稻草垛的芳香味,真的能俘虏你的味蕾,也能让从城市里来到我们农村的人,一下子迷恋这个小村。
在农村,父亲是堆稻草垛的高手,他堆的稻草垛最皮实,模样还好看。每年稻谷收割季节,对于我们农村的人们来说,都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之一。当人们把稻子从田间收割、脱粒之后,接下来就要处理大量的堆放在田间的稻草。那刚脱完粒的稻草穗头,软软的,摸上去如同丝绸一般的柔滑,它们被人们捆成小把子很随意地立放在稻田里,待稻草干了以后就把它不规则的一垛又一垛的堆在田间,正午的阳光很刺眼,映照在那些拥挤着的慵懒的稻草。
那时候我们农村大集体时期,生产队会将稻草分到户,社员们用夹拦将分得的稻草挑到自己家的禾场边,而父亲总习惯裸露着古铜色的脊背,肩膀上搭上一条黑里透着白的毛巾,手持着一支木羊叉,有板有眼地堆着稻草。按照父亲的老经验,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夯实地基最关键。他常常把计划堆放稻草的地方,用铁锨把那块地平整一番,再用木榔头夯实,铺上一层厚厚的沙子。之后双手抱着稻草,很均匀地铺上,再用双脚压实。待到稻草垛堆到近一人高度时,这就不是一个人作业所能胜任的,则需要两个人的协力配合,一个人在稻草垛下,用木羊叉叉起稻草,递送给稻草垛上的人,再由上面的人手持羊叉,接过一把把稻草,依次堆放。为了防雨,每每稻草垛“搭建”好之后,他总会用稻草盖成屋面样的斜坡,最顶端用一把捆得最大的稻草把子放在稻草垛上,形成一个尖顶,非常好看。
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稻草一直是我们农村人烧水做饭的主要燃料之一,而稻草由于长期堆放在室外风吹日晒,用其作为烧水做饭的燃料实在是不压火,家里的主妇们做饭时很头疼烧稻草,每每往地锅灶膛里续上一把稻草,可是稻草一沾火星,便发出刺啦的轻微的声音,倏然间擦出一道火花,就变成灰色的灰烬。为了让灶膛保持恒温,这就需要主妇们不停地续上一把又一把稻草。主妇们往往做一顿饭下来,常常汗流浃背,身上、头发上都落满一片又一片稻草以及灰烬,甭提狼狈不堪了。为此主妇们会让家里的顶梁柱们去砍伐树枝,茅草在院子里晒干作为灶膛里的燃料,晒干后的树枝最压火,还能有效地节省能源。
我还记得农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堆放的稻草垛,成为我们儿时的快乐天堂,我们在稻草垛里捉迷藏,有的小伙伴像一只钻山豹似的,用头猛力地往稻草垛深处扎,直到全身钻将进去,任凭你千呼万唤,我仍然躲在稻草垛深处。深秋时玩起捉迷藏,钻进稻草深处,尽管外面秋风瑟瑟,凉意袭人,但是人钻进去还是挺暖暖的,我记得有一次我钻进去,竟然睡着了,几个小伙伴扯着嗓子呼唤我的乳名,让我出来,我都浑然不知。当我睡醒后,听到母亲一声接着一声呼唤我的乳名,让我回家吃饭,我这才挣脱着稻草,像一只硕大的刺猬一般从稻草垛中拱出来。
后来小伙伴们钻进稻草垛里捉迷藏,有个小孩找不到钻进稻草垛里的伙伴,竟然擦了一根火柴,扔在稻草垛上,那燃着的火柴落在草垛上立马燃着了整个稻草垛,熊熊的大火燃烧一座又一座连着的稻草垛……后来我们生产队里的小伙伴们都不玩钻稻草垛的游戏了,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都烙印着深深的阴影,再玩钻稻草垛,那就是死亡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