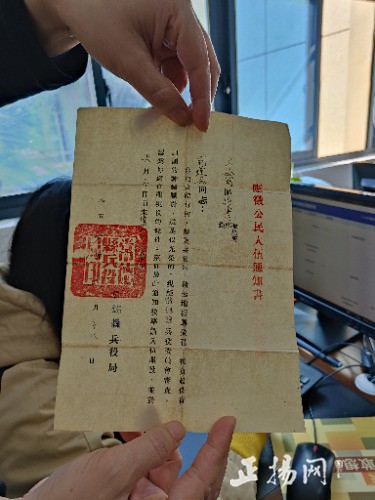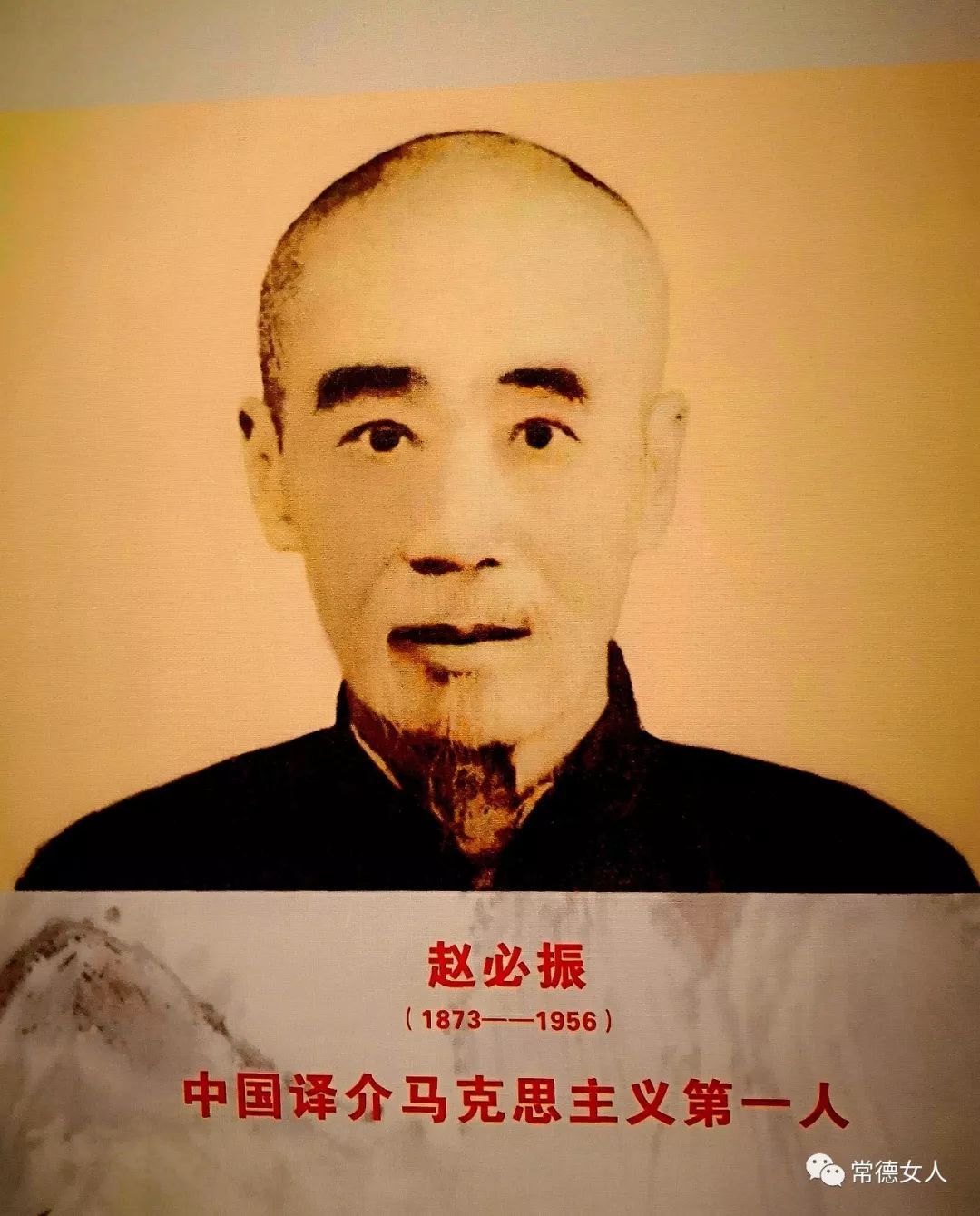从讨米要饭者的消失,看脱贫攻坚的成效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农家生活。记得小时候经常有讨米要饭的到生产队里,挨家挨户讨要,一般都是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拿出又破又脏的碗,社员们都会慷慨地给盛上一勺或一碗热饭。若赶上没有饭的时候,也会打发一把米,或者给几毛钱,不让他失望而去。
我离开家乡四十多年,如今社会的救助体系逐步完善,乡间已经没有讨米要饭的人了。
讨米要饭的也有真假之分。赶在饭点讨米的,不要别的东西,只要吃的,这是真正的讨米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群结队的讨米要饭的人来生产队,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人。或住生产队牛屋,或栖在稻草垛下,或宿身于旧砖窑中。还是有些幸运的,和当地社员们住在一起。他们有些是单身,有些携家带口的外地人。
到了七十年代,渐渐出现了另类讨米要饭的人,他们随时都可能出现,要钱要粮,甚至还有要粮票布票的,这类人往往是打着讨饭的旗号,把讨米要饭当无本生意来做了。乡亲们眼睛雪亮,真假讨饭的一看就知道。对真正讨米要饭的慷慨大方充满同情,而对那些好手好脚年轻力壮的假讨饭者则毫不客气,直接挥手拒绝。
再往后,到了八十年代,你会时不时遇到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穿戴整洁,手里提个十斤塑料油壶,笑容可掬地来到门前,掏出香烟,恭恭敬敬地递给你,说:“奶奶/爷爷今年九十几了,需要收百家香油给他/她祝寿消灾。”
还有一种特殊的讨饭者,乡亲们也一样待见。他们穿着不那么破烂,衣服虽旧但整整齐齐的,没个穷困潦倒的样子,反而带点书卷气。他们肩上挂着袋子,一手拿墨,一手执笔,走到每家门前,一声不吭,以墙做纸,提笔写下四行诗句,诸如:“行善之家,四季大发,家出贵子,高头大马。”或:“有福人,堂前坐,生贵子,上大学。”这些诗句寓意吉祥,颇符人意,而且朗朗上口,简单流畅,只要识字的都能看懂。所以遇到这样的讨要者不但没人拒绝,还乐意给点钱物,或一捧粮食,或一个馍,或几分钱。题诗者往往默默点头接受了,再赶往下一家。
我想,这类人可能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们粗通文墨,手无缚鸡之力,对付不了繁重的农活,也没有伶牙俐齿,找不到别的挣钱门路;家里或许有年迈的父母,嗷嗷待哺的幼子,他们才不得不放下尊严,拿起笔墨,走村串户,为家人谋得一点生计。
转眼四十年多过去了,当年题诗的墙壁早已更新换代,但那些黑墨渗入青砖的字迹,或拘谨,或流畅,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不知当年的题诗人,可安好?
老百姓的愿望就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今天我们做到了。但愿从此天下再无讨米要饭人。
我离开家乡四十多年,如今社会的救助体系逐步完善,乡间已经没有讨米要饭的人了。
讨米要饭的也有真假之分。赶在饭点讨米的,不要别的东西,只要吃的,这是真正的讨米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群结队的讨米要饭的人来生产队,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人。或住生产队牛屋,或栖在稻草垛下,或宿身于旧砖窑中。还是有些幸运的,和当地社员们住在一起。他们有些是单身,有些携家带口的外地人。
到了七十年代,渐渐出现了另类讨米要饭的人,他们随时都可能出现,要钱要粮,甚至还有要粮票布票的,这类人往往是打着讨饭的旗号,把讨米要饭当无本生意来做了。乡亲们眼睛雪亮,真假讨饭的一看就知道。对真正讨米要饭的慷慨大方充满同情,而对那些好手好脚年轻力壮的假讨饭者则毫不客气,直接挥手拒绝。
再往后,到了八十年代,你会时不时遇到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人,穿戴整洁,手里提个十斤塑料油壶,笑容可掬地来到门前,掏出香烟,恭恭敬敬地递给你,说:“奶奶/爷爷今年九十几了,需要收百家香油给他/她祝寿消灾。”
还有一种特殊的讨饭者,乡亲们也一样待见。他们穿着不那么破烂,衣服虽旧但整整齐齐的,没个穷困潦倒的样子,反而带点书卷气。他们肩上挂着袋子,一手拿墨,一手执笔,走到每家门前,一声不吭,以墙做纸,提笔写下四行诗句,诸如:“行善之家,四季大发,家出贵子,高头大马。”或:“有福人,堂前坐,生贵子,上大学。”这些诗句寓意吉祥,颇符人意,而且朗朗上口,简单流畅,只要识字的都能看懂。所以遇到这样的讨要者不但没人拒绝,还乐意给点钱物,或一捧粮食,或一个馍,或几分钱。题诗者往往默默点头接受了,再赶往下一家。
我想,这类人可能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们粗通文墨,手无缚鸡之力,对付不了繁重的农活,也没有伶牙俐齿,找不到别的挣钱门路;家里或许有年迈的父母,嗷嗷待哺的幼子,他们才不得不放下尊严,拿起笔墨,走村串户,为家人谋得一点生计。
转眼四十年多过去了,当年题诗的墙壁早已更新换代,但那些黑墨渗入青砖的字迹,或拘谨,或流畅,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不知当年的题诗人,可安好?
老百姓的愿望就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今天我们做到了。但愿从此天下再无讨米要饭人。